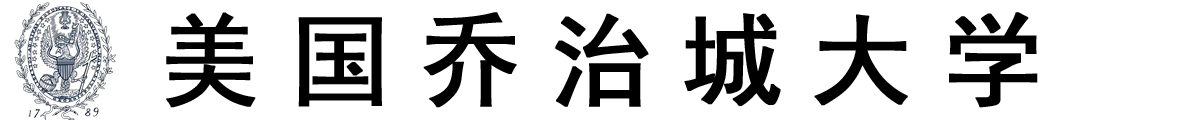拉比·阿拉梅丁现为美国乔治城大学客座教授及兰南基金会客座教授,今年十一月凭借小说《拉雅的真实故事(和他的母亲)》荣获享有盛誉的美国国家图书奖。
阿拉梅丁于2023年加入乔治城大学英语系旗下的兰南诗歌与社会实践中心,并于同年春季担任兰南医学人文学者驻校作家。他曾在2021年获得兰南文学奖。
《拉雅的真实故事(和他的母亲)》讲述了单纯善良的拉雅与母亲扎尔法共同生活在贝鲁特一所小公寓里的故事。通过拉雅的视角,这部小说勾勒出母子二人与黎巴嫩家园跨越六十年的时代变迁。
阿拉梅丁已出版七部长篇小说、一部短篇小说集及一部非虚构作品。《拉雅的真实故事(和他的母亲)》是他最新的一部长篇小说,于今年九月问世。其2014年作品《不必要的女人》曾入围国家图书奖决选名单。此外,他还获得2019年多斯·帕索斯奖、2025年出版三角协会比尔·怀特黑德终身成就奖,以及2022年笔会/福克纳小说奖。
文理学院于11月19日在纽约市的颁奖典礼后,对刚刚获得国家图书奖的阿拉梅丁进行了专访。以下对话经过精简与编辑,以提升可读性。
问:你并非在大学专修写作,是如何将写作融入生活的?
阅读始终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记得自己从小就一直沉浸在书中。父亲生前曾提醒我,四岁时他问我未来想做什么,我回答:“我想成为作家。”那时我对写作的理解,就是创作《超人》《蝙蝠侠》这类漫画故事,因为它们是我最早的读物。所以我一直广泛阅读,但真正开始写作,则是人生较晚的阶段。
我动笔写作,起初是因为对当时读到的内容不满。第一本书关乎艾滋病危机与黎巴嫩内战。当时正值艾滋病肆虐,而我对主流叙事感到不满,于是提笔写下我的所见。那本书《库莱兹:战争的艺术》就这样出版了。
问:你的写作动机是否随时间发生变化?
我常开玩笑说,自己写作是出于“复仇”——这其实是件积极的事。约四五年前,一家杂志采访我,并将我的一句话发布在社交媒体上。我不常活跃于那些平台,但有人特意转告我。那句话大意是:我写作,是想让幼儿园时没邀请我参加派对的孩子后悔;想让没成为我男友的人后悔;想让没请我去精彩派对的人后悔。我讨厌派对,但我渴望被邀请。
这虽是个玩笑,却一直留在我心里。不过说到底,我写作主要是因为我期待看到某类书,而它们尚未出现。既然没人写,那就我自己来。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一定更好,只是提供了不同的视角。
问:许多读者提到拉雅独特的叙述声音。你是如何塑造这一声音的?
这是个难题,因为我认为声音并非“塑造”而来,它本就存在,只是等待被发现。很多写作课教人“寻找你的声音”,我觉得这说法并不准确。你的声音一直都在,从未失去。
拉雅可爱之处在于,小说某些部分中,他只是坐着讲故事。如果故事本身精彩,自然能吸引人。当然,我做了一些处理,使其超越单纯的讲述。但今天我们不深谈结构技巧。第二部分几乎是纯粹的口述:一个人坐在舒适的沙发上,娓娓道来“这里发生了什么,那里发生了什么”。这就是声音的本质。
如果说声音是关键,那么它就是一个带着幽默感的叙述者。拉雅的魅力正来自他的幽默,尤其是自嘲的幽默。他嘲笑自己、母亲,乃至一切。
问:拉雅与贝鲁特这座城市的关系是怎样的?
贝鲁特至关重要。任何有价值的小说,其背景也必然具有生命力。拉雅对这座城市的感情,犹如对待一个反复无常的存在:它能给予巨大慰藉,也可能带来毁灭。面对这样一位“变幻莫测的神祇”或城市,关系自然会显得不稳定。
我想我们国家的问题之一,是以为一切皆可预测,却忘了生活本质充满未知。在贝鲁特,你不知道电力何时恢复、交通灯是否正常。而在德国或美国的某些地方,一切井井有条,人们容易忘记世上还有季风、地震这类不可控之事。我们似乎总未准备好接纳生活的随机性。
问:在一种推崇日常性、可预测性的写作文化中,你如何书写“意外”?
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无论是否在写作。我的作品也始终带有这种边缘视角。这并非指我不受尊重或欣赏,而是我不代表主流文化。尤其当我初试写作时,第一部作品曾令不少人惊讶。很久以后,才开始有人以类似的角度看待世界,其他作家也渐渐朝此方向探索。但这很自然:如果你决心写作,就该写下你所见的真实。
我成长于内战环境,又亲历艾滋病疫情,失去许多朋友。我曾组建一支同性恋足球队,三年内近半数队员离世——他们都是四十岁上下的年纪。因此我深刻体会到,世间并无绝对可靠之物,但我依然继续生活。按下电源键、电脑启动,这种小事也能让我感到安慰。
于是我渐渐相信一切会按预期运转,但心底某个角落始终清醒:事实并非如此。这份认知融入了我的写作。当我过于安逸时,会莫名陷入低潮——往往是因为困在自己的思绪里,足不出户。这时我会想:“我的烦恼真是天大的事。”而实际上,我需要主动置身于能提醒自己“生活不可预测”的境况中。生活并非总是平静安稳。
问:书中充满悲剧色彩。在悲剧面前,你认为艺术承担着怎样的角色?
简言之,这问题没有单一答案。艺术的角色极其多元:可以是娱乐、转移注意;也可以是见证、记录正在发生的历史;还有人认为意在启迪。文学与书籍拥有众多功能,不同读者各取所需。
文学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这场争论已持续几代人。莎士比亚究竟是为艺术而创作,还是仅为娱乐谋生?他的作品是否激发了人们原本不会有的行动?这是个深远的问题。
就我个人而言,当我坐下写作,思量的往往是如何让一个句子流畅起来,如何从这一处过渡到下一处,最终完成全书。我并非为某个既定目的而写。书成之后,一切就交给读者与作品本身。我并不确知写作的终极目的。
常有人引用埃莉诺·罗斯福的话:“生活的目的是活得精彩。”或许同理,艺术的目的是创造,文学的目的是书写。其余皆是衍生。